
2002年,我從紐約飛到波士頓去參加哈佛燕京社舉辦的一個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座談會,見到了來自三藩市的陸鏗與崔蓉芝。感覺上,陸鏗說話反應有點遲鈍,連自己寫的稿子都念不清楚。同十多年前在紐約中國城餐館裡見到的他不一樣。那時他是神采飛揚,聲若洪鐘。後來我才知道他已有了阿茲海默症的初期徵兆。崔蓉芝比起八十年代在報紙上見到她的樣子,明顯是發福了。在中餐館吃晚飯時,她忙著給坐在她身旁的人布菜,就像是一個慈祥的猶太母親。
當時在座,沒有人提到江南。
兩年之後,我在中文報紙上讀到她紀念江南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水落石未出」。足見江南仍是她魂縈夢牽的。江南被謀殺是沉澱在她心中無法忘懷的痛。
世襲專制緣起緣滅
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芝加哥市郊的Cantigny莊園內的「第一師博物館」研究中心,獲得了美國報業鉅子,《芝加哥論壇報》發行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與曾任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兩家人的往來通信檔案,一共九十封信,時間從1948年到1955年。此外還有美國《生活》雜誌對吳家長女(修蓉)在Cantigny莊園結婚的報導與攝影剪輯(1952-6-30)等資料,以及吳國楨與蔣介石決裂時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英文聲明原稿。吳國楨同麥考米克的通信,從討論上海的時局,到如何把臺灣建成亞洲的民主堡壘,到吳家女兒赴美留學,麥考米克夫婦自願充當監護人,一直持續不斷。最後,吳國楨在美同蔣家政權公開決裂時,處在臺北國府、駐美使館和中國遊說團的重重壓力下,麥考米克夫婦是對他仗義相助的「黑馬」。
1948-1955年正是中國內戰到國民黨潰敗遷台的大轉折時期,而這個大轉折決定了臺灣往後數十年的政治命運。世襲專制在臺灣的孕育成形,吳國楨無疑是個見證人。在這個過程中,他奮力抗爭,終不免敗下陣來。
以這些通信為經緯,我閱讀了一些資料,做了比對研究,完成一本書稿,《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今年四月由臺灣允晨文化公司出版。

江南之死
在寫作期間,我覺得「緣起」的部分比較容易掌握,反而是「緣滅」的部分,對我來說,仍有一些疑惑,特別是作為關鍵因素的江南命案。所以去年十一月下旬,我在臺北用電郵與四十年未見面的柏克萊老友李乃義聯絡。李兄是加州矽谷成功的企業家,現已退休,在矽穀和上海兩地居住。接到我的電郵時,他正好人在上海。兩天后他就從上海飛來臺北,在新生南路的紫藤盧與我見面。
李乃義是吳國楨生前在喬治亞州薩瓦娜接待的最後兩名訪客之一。1984年3月17日,李陪同江南走訪吳國楨,談了兩天,總計12小時。此後幾個月江南在朋友面前聲稱,他得到不少寶貴資料,準備寫吳國楨的傳記。江南首先整理了他對吳國楨的訪問記,在紐約出版的一本華人刊物《臺灣與世界》第12期(1984年6月號)刊出,題目是「吳國楨八十憶往」。繼而又在該刊第13期(1984年7-8月)刊出「吳國楨逝世前的一封信」。吳在信中又細述了他兩夫婦1953年所遭「汽車謀害」的經過,糾正了江南的一些報導錯誤。吳還透露他在台被扣為人質的小兒修潢,最後出國來美前,蔣經國還打算派人將他的腿打斷,使他成為殘廢,幸而黃少穀善言規勸,才打消此議。「弟與內子對此均感激少穀不盡也。」

十一朵曇花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發生後,江南好友李乃義是治喪委員會的一個主要負責人。我請他追憶當時的情況。他告訴我的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原來,命案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李乃義在江南的大理市(Daly City)家中吃飯。他向我強調,他是學科學的(柏克萊核子工程系),從來不信靈異鬼神那一套。可是那天晚上,他感覺到江南似乎情緒很煩躁,沒來由的,(印堂發黑?)晚飯後聊天,近午夜時分,他家客廳的十一朵曇花忽然盛開。江南要崔蓉芝拿剪刀把曇花都剪下,煮水給李乃義喝,因為他喉嚨多痰(抽煙的緣故?)崔蓉芝捨不得剪花。江南就拿起剪刀「哢嚓、哢嚓….」,十一朵花全剪下來了。
當晚臨走前,他在洗手間洗臉,手錶留在盥洗台忘了帶走。回家想起,心想第二天到三藩市上班途中可以彎過去拿。結果第二天早上,車開在高速公路上,一晃神,竟錯過了大理市出口。
到辦公室不久,中共駐三藩市總領事唐樹備打來了電話。唐樹備本來當天中午與江南有飯約,但突然接到江南的大理市家中來電說,江南當天將無法赴約。講電話的是一個洋人口音。唐接到訊息後,意識到江南家中可能出了狀況。他立即分別電告李乃義和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圖書館主任陳治平,希望他們抽空到江南家去看一趟。李趕到大理市,見到痛哭流涕的崔蓉芝,忙著安慰她。大理市警局刑事探員正在命案現場搜證。由於這是一起不尋常的謀殺案,既非打劫行兇,又無財物損失,女主人指出,江南不久前才出版《蔣經國傳》,這個證詞指向了政治謀殺的動機。美國聯邦調查局也迅速介入了調查。

李乃義從警局探員手裡取回他的手錶。連載《蔣經國傳》的《加州論壇報》副社長阮大方也從洛杉磯趕來。李乃義自承他是左派、統派,阮大方是主張革新保台的右派。臺灣當局先前還透過阮的父親,《中央日報》前社長辦阮毅成,要其子中斷在《加州論壇報》上連載的《蔣經國傳》,受到婉拒。但在江南命案上,兩人一左一右,初次見面,竟成莫逆之交。在記者招待會上,兩人同聲指責國民黨幹下了這件令人髮指的罪行。
FBI人員和大理市警方聯手,一個星期之內就破了案。但他們要求兩人暫時不要在記者會上透露消息,因為有些線索尚未收齊整理好。
「如果你當天早上從大理市出口轉出去,豈不是會當場撞見殺手的行動?你也可能遇害呢!」我問。
「這不無可能,但既然是政治謀殺,殺手顯然不願意把事情變得複雜。他們先前已經租了腳踏車在江南家附近勘察,如果我在他們下手之前去到,也許他們就推遲計畫的行動了。」
江南命案,從後續發展來看,美國華人沒人相信當時竹聯幫殺手是主動「為國鋤奸」,也沒人相信不久前才從駐美武官調回臺北升任國防部情報局長的汪希苓,會自作主張,利用幫派在美國執行暗殺任務。在美搞情報的汪希苓是瞭解美國情況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謀殺一個美國公民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雖然在駐美武官任內,汪曾通過《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傅建中牽線,同江南談判,要他刪改著作。美國公民江南對汪的命令式口吻和盛氣淩人的態度,甚為反感。

人們普遍的推測是,在情報局的層級之上,還有真正下令或授意之人。江南若繼續寫出《吳國楨傳》,再爆內幕,對國民黨多年在台經營的蔣經國形象,顯然更加不利。這個真正下令或授意的「藏鏡人」,也正是崔蓉芝後來質疑的「水落石未出」的關鍵所在。
關鍵的軍售問題
1984年12月中旬,掌握了充分證據的聯邦調查局向國務院報告,指出臺灣國防部情報局捲入江南命案。眾議院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Steven Solarz)宣佈要舉行聽證會,討論是否停止對台軍售問題。三年前(1981)眾院為陳文成在台離奇死亡案舉行的聽證會上,索拉茲就提出了有關對台軍售的「修正案」(《武器出口管制法》索拉茲修正案),因為不能容忍臺灣政府違反《臺灣關係法》,侵犯人權和抵觸美國法律的行為。現在,臺灣官方人員竟派人來美國進行恐怖活動,顯然構成停止軍售的理由。
國務院要求國民黨政府將已返台的陳啟禮、吳敦引渡到美國加州受審,但台方以不符引渡條款第四條的規定為由,拒絕此一要求,但同意配合美方的偵查作業。蔣經國本來是打算拖延觀望一陣的,但美國聯調局擠牙膏,對台出示了更多的證據。而也就在這段時期,1985年1月13日,在美國的竹聯幫成員白狼中向聯調局交出了陳啟禮留下的一卷錄音帶。
情況至此急轉直下,蔣經國只得下令將涉案的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和處長陳虎門免職。同時政府公開發表聲明,承認對情治人員的涉案「非常震驚」。
從免職到實際扣押的期間,臺灣當局似乎已同汪希苓談了條件。這就是傳聞所說的,蔣經國要汪獨自為國家扛起責任,「好好想想對外面的說法」。汪多年後接受訪問時表示,在他受軍法審判被判決無期徒刑入獄之前,蔣經國曾召見他:「你知道嗎,關我以前,蔣先生找我去談了半個鐘頭。我說不要考慮我,為了國家,我願擔起一切責任。蔣先生也不願把我關起來,他也很難過,這你就懂了。」
然而,回到當時的場景,即使汪要獨自「為國家扛起責任」,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他還必須通過美國來台辦案人員的測謊器。
未通過測謊
本來,在聯調局出示了證據後,台方只得讓聯調局兩名探員和大理市警局刑事組長前來,最初是限於就「謀殺行動」的刑事部分,約談陳啟禮、吳敦,並進行測謊。但不包括情報局涉案人員。
可是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一開場就群情洶湧。加州日裔眾議員本田(Mike Honda)憤慨指控,眾議員藍托斯(Tom Lantos)強調,如果確定江南的謀殺案是臺灣當局「針對在美人士的恐嚇騷擾的一貫行為模式」,則國會就應根據「索拉茲修正案」,切斷對台的武器銷售。
迫于情勢,蔣經國只好改變態度,允許美方人員也約談情報局長汪希苓,並進行測謊。汪有沒有明白下令殺害江南?有沒有上級同意這個謀殺行動?對這兩個問題,他都否認。但在場的美國在台協會政治組人員注意到,汪在回答時明顯「局促不安」,測謊器顯示他在說謊。(陶涵,2000:432)不過,美方人員表面上不動聲色,沒有深究下去。
汪希苓是在為他背後的「藏鏡人」掩飾什麼嗎?在政府表示「震驚」,蔣經國表示「震怒」的表面宣示下,到底蔣經國事先是否知情?耐人尋味。
在美國眾議院就「軍售」問題舉行聽證會時,蔣經國就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將涉案的情報局官員免職後,對外宣告政府決不惜代價,毫不隱瞞地依法嚴辦,同時還成立了以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汪道淵、國防部長宋長志、參謀總長郝柏村以及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組成的五人小組,來負責調查。據稱他也曾向他的親信郝柏村吐露,「劉(江南)案理不直,處理事難上加難、痛上加痛、苦上加苦。」

但問題是,不管說什麼「痛上加痛、苦上加苦」,「嚴辦」到最後,普通法院和軍事法庭的檢察官都「適可而止」,沒有人去追究汪希苓是否「奉命行事」,在汪之上,是否還有涉案的人。五人小組的調查自然也無結果。一切似乎都按劇本演出,有官職在身的情報局人員,發起「制裁」行動,竟是出自「私人動機」,也是夠荒謬的了。黨外刊物提出質疑,結果是雜誌全數被警備總部沒收。
三面間諜
在江南命案的涉案殺手和情報局官員受審之前,臺灣當局的「損害控制」機制,也開始運作。由當時總統府秘書和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主導,試圖把江南案帶到一個新的方向,以轉移國際媒體的焦點。不久,合眾國際社自臺北發出消息,指稱江南其實是臺灣國防部情報局的情報人員。美國《新聞週刊》與《時代週刊》也報導江南是美國聯調局線民,負有監視在美華人動態的任務。《聯合報》1985年1月25日搶先刊出江南生前寫給情報局的一封信原件影本與簽名。
繼而,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在1985年2月號刊登了江南寫給情報局的六封信和寫給他從前在《臺灣日報》的老長官夏曉華的一封信。這七封信據稱是夏曉華與《九十年代》編輯人員在東京約見時交付的,經總編輯李怡核對筆跡無誤。江南是《九十年代》的長期作者。此時又傳出江南是中共方面的間諜,七十年代中期他已進出大陸。
這一連串聳動的新聞立刻蓋過了當時美國東西岸集會抗議的主題---外國政府在美進行恐怖活動,以及華裔美國公民人權與人身安全的訴求。江南的《蔣經國傳》沒人提了,他打算寫的吳國楨傳也無人理會。夏曉華這個軍統老特務的及時出山,為國民黨立了大功。江南的形象從民主鬥士變成三面間諜,至少使人懷疑江南案不是一樁單純的政治謀殺案。

然而,「損害控制」的效用並沒有持續太久。去過大陸的人給美國聯調局約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不會自動成為「線民」。在三藩市魚人碼頭開禮品店的商人,到大陸去尋找商機,也是合情合理的,會變成「間諜」,難道不是臺灣情報局為「制裁」而找理由嗎?收了「改版費」居然不改版,就像當年辜鴻銘收了賄選的錢拿去逛窯子卻不去投票,一樣的可惡。對情報局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給臺灣情報局的情報信「彙報」的對象,如金山灣區的張富美、陳鼓應,都公開指斥所謂「彙報」的內容皆為編造的故事。這就回到當初臺灣情報局透過夏曉華出面安排,希望江南修改《蔣經國傳》而願支付的「改版費」了。當初談妥八千美元的「改版費」之外,夏曉華為照顧老部署,還為他爭取到寫「情報信」,由情報局每月支付一千美元的津貼。接近情報系統的人後來透露,所謂情報信就是江南將他在三藩市灣區聽到的消息見聞,提供給夏曉華,轉交情報局,其實根本算不上什麼機密情報。香港《信報》的吳姓評論員看了那些情報信後,哈哈大笑說,那種信他一天就能寫七八封。這是向情報局「訛詐」嗎?夏曉華已死,問他兒子夏鑄九去吧。
宋楚瑜主導的挽救蔣經國形象的努力,在宋楚瑜主導下,雖然處心積慮,到頭來,經國的形象還是碎了一地。
經國還是孝武?
是誰下令(授意)謀殺江南?陸鏗1996年為台版《蔣經國傳》寫的序文「江南不死」,已認定江南是蔣經國下令殺害的。李敖認為「最大的可能性是,蔣經國事前默許,事後掩遮。即使退一步說,他事前不知,也難逃道義上的責任。」楊青矗根據殺手吳敦返台「述職」,向汪希苓報告完成任務後,見到汪畢恭畢敬地打電話向「上級」報告的神情,因而推測下令謀殺的必定是蔣經國。後來蔣對江南案的「震怒」,可能是氣惱特務把事情辦糟了。
蔣經國對江南這個政工幹校高材生,無疑十分痛恨。以他過去呲睚必報的性格,大陸易手後,人在上海的臺灣火柴公司董事長吳性栽出資拍了一部醜化蔣介石的影片,他就把毫不相干的臺灣火柴公司總經理抓來判死刑。但從政多年,當了總統之後,他還會像年輕時那樣衝動嗎?
以汪希苓對蔣家主子的「忠」,他畢恭畢敬的報告物件,不也可能是蔣孝武?蔣家侍從翁元曾著書指出,蔣孝武繼承了他父親「特別愛記恨」的性格。美方駐台人員收集的情報顯示,蔣孝武當時藉著他的特殊身份,到處插手管事。他是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又是國安會議副秘書長,憑父威在媒體演藝圈頤指氣使,在情報系統呼風喚雨,成為畏懼與依附的物件。而竹聯幫份子插手於電影製片行業,在臺灣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由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出資,蔣經國基金會贊助,由美國退休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撰寫的《蔣經國傳》,在處理江南案上,也是循著這個理路。陶涵稱讚蔣經國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基本上,他不相信蔣經國對謀殺行動事先知情。他採信的說法是,三個竹聯幫殺手完成任務,1984年10月21返台時,接機的情報局官員陳虎門稱讚他們幹得好,「大老闆」很感謝。據陳啟禮對他的弟兄董桂森所說,「大老闆」是「蔣孝武」的代號,「小老闆」是「汪希苓」的代號。這有可能是來自聯調局的蒐證材料。1996年,某位接受陶涵訪問的「蔣經國的多年親密同志」,證實汪希苓的確在「替某人掩飾」。與陶涵談話的「幾位當時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信,原本的點子出自蔣孝武。」(陶涵,2000:432)同年6月7日,陶涵訪問蔣緯國談到蔣孝武是否涉及江南案時,得到的答案為:「是的,有可能。」(陶涵,2000:440)以這本主要在誇示蔣經國功績的傳記來說,這應該是有說服力的。陶涵從接近蔣經國的一個消息來源聽到,蔣彥士1985年2月從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位下臺,是因為他答應看管孝武卻沒盡到責任。陶涵用了「看管」兩字。一般人的理解是看管孩子。但蔣孝武當時已是四十歲的中年人了。
1985年期間,白宮的日子也不好過。雷根總統為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抗軍」的問題,(亦即把對伊朗的違憲秘密軍火交易獲得的錢用來資助企圖顛覆尼加拉瓜左翼桑定政權的「反抗軍」)受國會糾纏不斷。因此透過臺灣駐美代表錢複對台暗示,只要臺灣願意通過某個管道間接對「反抗軍」提供一百萬美元的捐助,白宮就會樂於幫臺灣解套,讓江南案在美儘快落幕。(陶涵,2000:440)蔣經國當然喜出望外,通過「世界反共聯盟」的白手套秘密送去了捐款。臺灣表面上仍和尼加拉瓜的左翼政權維持外交關係,也有官方援助計畫。此舉等於兩邊下注。
1985年6月,美中(台)經濟協進會理事長大衛·甘乃迪夫婦訪台,帶來了雷根總統的正面訊息。
蔣經國:關於劉宜良(江南)命案,你一定瞭解,這可說是想像不到的事情,我感覺非常憤怒、遺憾。這不但在國內有影響,在國外更是造成我們形象的莫大損失。我們已經努力在司法、軍法上確實做到公正、公開、確實的、不隱瞞的處理,希望能平息各方面的憤怒。甘乃迪(與甘乃迪家族無關聯):我知道總統你及貴國對劉宜良命案的處理,非常理想。我瞭解雷根總統已經接受你們處理的方式,因為他知道貴國是以非常公開、公平的態度在處理,儘管在美國還是有一些批評,但是再過一些時間,就會過去的。
在談話中,蔣經國表達他希望美國政府瞭解「軍售問題對我們的重要性」。(國史館005-010303-00018-011)

然而,美國國務院顯然並不以眼前的「解套」為滿足。國會「軍售問題」的聽證,聯調局對江南案的秘密偵查報告,在對台政策的長程規劃上,都是可用的籌碼。在老病體衰的蔣經國身後,國務院不希望臺灣在憲政體制之外,再出現社會所傳聞的「蔣三世」繼承人,將來實際掌權。
從江南案審判結束後不久,蔣孝武就被「放逐」到新加坡擔任商務副代表,在時間順序上,並不令人感到意外。1985年8月,蔣經國在《時代》週刊記者面前宣佈他的子女不會接班。這一年12月,他又在國民大會年會上重複聲明這個立場。從美國掌握的籌碼來看,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
蔣孝武致父家書
今年初,我到國史館去查看國防部情報局(後改名軍事情報局)當年的行動資料,全無頭緒。倒是在蔣經國檔案中讀到蔣孝武從新加坡寄回的家書。
這是一個失去了熟悉舞臺的中年人給「父母親大人」的信,「今年(1985)八月十八日是兒抵新加坡就任滿半年之日,回想半年來無論在公在私,都有許多意料之外的變化。」而這年十月是「祖父大人百齡紀念」,他「祈請大人賜知」,「兒等到時是否應返國參加。」總統府秘書室主任王家驊給他寫了回信,「謹奉指示,請於十月十八日(即農暦誕辰九月十五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國暦誕辰)任擇一日返國。」只准回去一天。
另一封信:「兒在此已一年,陌生感已消失,一切也都能適應,但是究竟不是自己的國家。」他的舞臺不在這裡。他又有所感,「今天在復興基地的同胞,都應有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的自覺。」(1987-2-11)
這大約是他老爸愛聽的話。秘書室主任王家驊回了信,「總統閱後,深表愉快」,但囑咐王奉達的是「尚望益自惕」。(1987-2-17)
另一封信是祈求老爸能對他諒解:「今天雖因為外在的因素使許多事情出現複雜而難以處理的情況,但一思及大人的教導與愛護,就能再鼓起勇氣來面對一切,以冷靜的思考去分析問題,….」(1987-9-14)
還有一封信是藉著中秋團圓日,向他父親祝賀佳節。在這封長信中,他也抒發了心中的感受:
「因閱及各項有關國內的報導而困惑萬分,兒想到原本是黨是政府為全體民眾所設想的種種良策善政,但卻又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與(予)以歪曲,而更可悲的是還有人去盲從,真可說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兒日夜省思,認為其中有兩點是最為可憂的,一是新聞媒體誤導民眾,借言論自由為名而實在卻傷害了國家社會,今天與(輿)論已非公器而成為少數人的工具,一是人們在過於安樂的生活中失去了理想和理智,而只追求眼前的欲望,…」
「…除大人外,兒又能向誰傾述,祈請寬恕兒之不當。」(1987-9-28)
這樣的訴怨,似乎是要討他老爸歡心。對他老爸來說,也許是中聽的。臺灣人民的生活「從未有像今天如此富足過」,但卻「人在福中不知福」,不知感恩。尤其是新聞媒體誤導民眾,對「黨和政府」的「良策善政」,刻意歪曲。這種想法也是蔣家人的一貫思路。江南寫的《蔣傳》無疑也屬別有用心,傷害國家領導人的罪魁禍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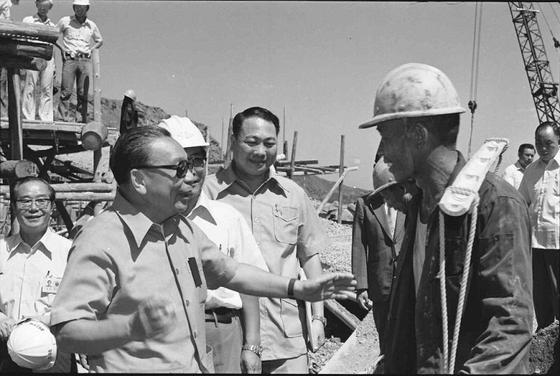
不過,對蔣孝武「叩呈父親大人」的這番感受,「奉示復函」的秘書室主任王家驊,只簡短轉告總統獲悉後「甚表慰勉」而已。回函日期是1987年10月1日。看來,蔣經國的身體狀況可能已經不行了。
其實,在蔣經國連任總統之前,健康情況已亮紅燈。黨外雜誌不少文章都規勸他不要連任。蔣經國和國民黨強硬派的答覆是嚴厲打壓,收繳雜誌。問題是,還有政權的「法統」問題要解決,體制不能不改革,政治權力不能不調整。當時在臺灣被視為「老賊」的萬年國代立委,還能再混下去嗎?
由改革呼聲所形成的大氣候,顯然已無法靠對「美麗島」運動的反撲,沒收黨外雜誌,殺害林義雄家屬與陳文成、以及謀殺江南等恐怖手段來壓制的了。
水落石出了嗎?應該是的。
坐在臺北長沙街的國史館檔案室內手抄蔣孝武的家書,我覺得有點荒謬的感覺。(「數位檢索系統」的資料只能在電腦螢幕上看,不能照相,不能影印。)蔣孝武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在臺北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口的龍安國民學校讀五、六年級時,班上轉來了一個小洋人,引起不小騷動。他是有兩個保鏢坐中型吉普車送他來上學的轉學插班生,是個小惡霸,已經轉了幾家學校。我們在學校後面翻牆翹課,被訓導主任抓到,必須罰跪在竹掃把上。蔣孝武下課時在後門吉普車旁,玩著保鏢的槍,所以在學校沒人敢惹他。
據說後來中學畢業後,他上了陸軍官校,老蔣總統還親筆寫信嘉勉他。不過,念了沒多久,就因不遵守校方訓練作息課程而遭退學。但他也竟能不經聯考而「插班」輔仁大學。與我同年的任顯群女兒任治平在為她老爸作的傳記《這一生—-我的父親任顯群》中,對蔣孝武轉學輔大工商管理系,有這樣的描述:
開學沒多久,班上來了位新同學。新同學到校那天派頭極大,我在法學院二樓陽臺上看到有兩輛凱迪拉克大轎車開進校園來,非常搶眼。兩輛車直接開到法學院宿舍,一看竟然是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他原先念陸軍官校,現在轉到輔大來,而且要念工商管理系和我同班。他由叔叔蔣緯國陪同下車,消息馬上傳開。教官很緊張,先帶蔣孝武選宿舍,他選了之後,教官就通知原先已入住的同學搬出去,改住另外一間,所以那位同學很火大。…臺北的陳世瑜同學抱怨:「我們考得千辛萬苦才進來,為什麼他隨便就可以進來!」蔣孝武的插班,連考都不用考,他的到來引起班上同學不快,聯名寫信抗議,…沒多久,文學院龔神父帶來情治人員到家裡來找我調查此事,因為我是班代;…蔣孝武開始上課,我們班上的都不理他。他遲到,上課另有兩個人跟著進來,我們全班才四十個人,非常顯眼。我看那兩個年輕人不像保鏢,應該是他的玩伴之類,陪他過來念書的。蔣孝武只在我們班上待了兩個星期,就不再來了。(任治平,2011:49-50)
蔣孝武后來的學歷上有「德國慕尼克政治學院」。他何時去的?有沒有學籍?拿到了什麼學位?這些問題大概都是經不起「深究」的。
我們只知道他後來回國後,曾在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任職,不久到「劉少康辦公室」,進入國安情報系統「歷練」,1980年任中廣公司總經理,1984年為國安會議副秘書長。1986年3月被調派為駐新加坡商務副代表。1988年蔣經國死後,繼任總統的李登輝1989年年初,將他提升為駐日代表,算是「蔣經國學校」出身的李登輝的「知恩圖報」。1991年6月,新任的李總統正式提拔蔣孝武為華視董事長,讓他終於回到闊別已久的熟悉舞臺。但就在他7月1日上任前夕,在陶陶飯店與酒友的飲宴上,患有嚴重糖尿病而又煙酒不離身的蔣孝武,突然出現緊急情況,送醫急救。7月1日淩晨死於心臟衰竭。
俱往矣!
*作者為旅美作家。本文為作者新著《誰怕吳國楨》後記
——风传媒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